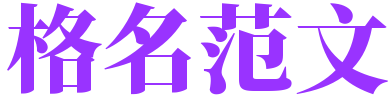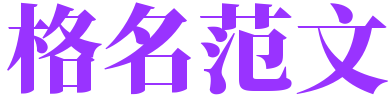月亮知音一样地懂我,睁大了眼睛,望着田畴、村落和山岗,她那银盘似的脸,流露着柔和的笑容———空灵、明静。这空灵、明净的月光,让我想起了弘一法师,想起他在病中与诸友最后告别时说的一句偈语:“但只见春满花开,皓月当空,一片宁静安详,那就是我的归处啊。”
靠在车座上,依窗侧望一路跟随的月亮,我心里自问,当初,那位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的翩翩浊世佳公子,那位风流倜谠的留日才子,那位学贯中西的大艺术家,以怎样的决心和毅力,毅然决然地从热汤热炕转向青灯黄卷,如何能断食断欲、斩断尘缘?本是锦衣玉食的翩翩公子,绚烂之极瞬间归于平淡。丰子凯说李叔同的出家是为追求“人生的第三层:灵魂生活”。其一生正如赵朴初先生的评价:“无限奇珍供世眼,一轮圆月照天心。”

于是,我笃信,大师归去的那一刻,是受到了明月的点化,所以从容,所以淡定。今夜的月,依然附着那颗高贵、通透而狐独的灵魂,是李叔同先生的,也是弘一大师的。
难怪张爱玲说:“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,我从来不是的,至少,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,我是如此的谦卑。”是的,弘一法师的月亮,如银碗盛雪,不染一点尘埃,在高贵、通透的灵魂面前,即便是一代才女,乱世佳人,也高傲不起来。
月亮不因世浊世清,一如当初空灵明澈,无数人对它敬之爱之,皆因她能抚去我们心中的污淖,让心宁静。
多年前,看过那幅《星夜》油画,那巨大的、卷曲旋转的星云,那一团团夸大了的星光,那一轮令人难以置信的橙黄色的明月,正从月蚀中走出来,混乱又抽象。想来,寂寞而疯狂的凡高内心一直痛苦的,挣扎的,那份独孤求败、无人能懂的狂傲,让他在浊世里迷失了自己。“上帝是月蚀中的灯塔”。与弘一法师一样,月在凡高的眼里也具有不可玷污的神性,他渴望上帝的拯救,却再也无法回到心地澄澈、清辉映月的从前,彼时,他心中圣洁的月亮正经历着一场怎样的生死分裂呢?月亮病了,因此,凡高的月亮有点凌乱,有点浑浊,像坠落尘埃的天使。
其实,月亮还是那个月亮。
车子行驶在回家的路上,路旁的原野寂静、河流寂静、村庄寂静,远处的山近处的林都寂静,只有我的内心世界与汽车的马达一样异常地喧闹。在这样的华月满天、清明澄彻的纯净夜,俗世中的我们,有多少人能平息内心的喧闹呢?“江畔何人初见月?江月何年初照人?”当初,诗人的内心也一定既是无限地孤寂,又无限地喧闹吧。此时此刻,我亦如此。
生命的闪耀仅停于瞬间,而生命的流逝才是永恒。因此,许多人在生命最绚丽的时候,都想把握点什么,留住些什么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天下攘攘皆为利往,在生存竞争激烈,物欲横流的当下,人们为名为利奔波忙碌,有谁能静下心来发出心灵的叩问:活着,究竟是为了什么?
于娟,这位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年轻教师,生病之前的30年,她的生活高歌猛进———读书,考研、读博、留学,她像一只赶路的鸟儿,忙着去追赶一个又一个目标,直到有一天被命运掐着脖子按在尘土里,她才懂,硕果累累的半世浮华,原来只是一场梦。2010年1月她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,在她离开人世之前,在体会了种种逼近极限的痛苦、悲伤、不舍、不甘等情绪之后,她用犀利而幽默的文笔,记下病中种种经历,剖白自己的内心,在她人生的末日,才开始了对生命的思考与叩问。梦醒时,已是曲终人散。
人的生存欲望、眼前利益、局部需要一旦被社会性地突出之后,就越来越远地偏离了自己的生命初衷,背离了自己的灵魂指向。太多现代人少了思考,很多问题因为生活节奏太快,而来不急去想来不急去问。人们总是在不停地往前冲,以为前面有很多东西在等待我们,不愿给心灵留下一点点空闲的时间,就连仰望这高悬于头顶之上的明月,似乎也是一种奢侈了。其实,很多东西是在我们的身后,蓦然回首,才知道,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。
我们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月亮了,我们的心中,不知道还有没有那轮明月。
开车的师傅提醒我到家了。此刻,月儿正泊在小城的群楼之上,像晶莹剔透的明镜———月下的小城祥和而宁静。